
三年前,出差上海,堂姐的女儿带着她的男友晓存到宾馆看我。
小伙子长得挺帅,我端着长辈架势问:“什么地方人啊?”外甥女说:“我们老家的呀,大学毕业后也在上海工作。”哦,老家哪个乡镇的?他说,大隆。我笑了:“巧,熟呢,我在那里工作十年,你们家大人也许我认识。”晓存说:“我的外公叫顾西怀,当过大队支书。”
“哦,他家女儿好几个,你妈排行老几?”我问。晓存说,我妈是老大。我大吃一惊:“那你上面还有个姐姐对不对?”晓存好奇:“是的,您认识我妈?”我说,何止认识,你妈是舅妈的朋友,哎,何必报你外公的官职,你的名气比他大得多!外甥女莫名其妙:“舅舅,我们初出茅庐,您可不带这样取笑人啊。”我说,他一出娘胎便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,你不知道?
也许因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,其父母不愿意提及,孩子们不知情。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说,那天也就没有就此深谈下去。

近来我在研究“只生一个好”与“鼓励生三胎”课题,不禁想起当年那个轰动全乡的“小超生游击队员”。前天晚上,我微信外甥女:“丫头,给你布置一个任务:代我向你婆婆问好,就说我想了解她当年生养晓存的经过情况,请她介绍一下,你做好记录,近两天发给我看。”
外甥女不折不扣完成了任务,今晚发来晓存母亲如泣如诉的回忆——
1982年我怀了第二胎。生产队长说没有生育计划,要我去引产,承诺第二年给生养名额,我信以为真,就去引产了。
1983年,我又怀孕了,当时我在公社服装厂上班,生产队干部追到厂里软磨硬泡还要我引产,我怕丢掉社办厂工作,只好又一次把孩子打掉。我老公是大队赤脚医生,他当然是懂避孕办法的,我们只是想碰碰运气,看能不能侥幸让我家再生一个孩子,给女儿作个伴。大队抓计生的副主任看出了苗头,要我老公去做绝育结扎手术,我们没同意。
1984年我再次怀孕,铁了心要把孩子生出来。怀孕期间我躲在家里不出门,对外谎称去了王港乡服装厂。直到这年夏天即将足月生产,我才秘密转移到城郊姨娘家避风。
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,被抓生育的干部晓得了,逼着我那当大队妇女主任的三妹带路找我。三妹受他们管,不敢违抗。那天,好大的阵势,乡里、村里、生产队出动了好多人,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坐拖拉机,一路奔来直扑我的藏身地,抓住我后直接押往县计生指导站。
我坚持要等老公到场,否则誓死不配合,他们只好去找我老公。老公躲在他姐姐家,还是被他们抓到了。晚上,我们家“夏医生”来到计生指导站。无法抗拒,在干部们的监督下,医师给我打了催产针。稍后,我感觉要生了,老公悄悄嘱咐我,坚持,千万不能声张。
过了大约一小时,指导站医师过来问“有没有要生的感觉”,我说没反应啊。那就再等等吧,他们送来一顶军用式蚊帐,不透明,整个罩住床,外面人看不见里面人。“夏医生”机灵,乘人不备踢了一只干的布拖把到床底下,然后钻进帐子悄悄为我接生,我咬着牙一声不吭。放在床下的布拖把正好吸着我淌下的血水不外溢,所以尽管干部们频频转悠,就是没察觉。
孩子生出来了。一声响亮的啼哭,传遍病房内外。
看守在病房门口走廊里的干部们大惊失色,那个人称“洋辣子”的乡计生干部跺脚大叫:“这哈子没得命嘞!”随即冲进病房撩帐子,我赶忙跃起身子,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,老公则迅速用嘴咬断牵连在我和孩子身上的脐带。
大队干部奔去喊医师来处理。医师来了,见我已生下活婴,对干部们说:你们没看好,现在孩子生了还能怎么样?你们不负责任,不能影响我们计生指导站的声誉,必须立即出院!
干部们急得跳脚,忙向上级报告,我们乘机抱起娃娃就走。
过了半小时,乡里领导来了,说“如果大的小的出了事,我们的责任就更大了”。看守人奉命追赶,传达要我们回计生指导站命令。此时,我强忍疼痛已一步一个血脚印走了二里多路,但我们知道,只要回头去,他们就会变着法子整死我的孩子。我们死活不肯回头。我老公说,我是一家之主,我也是个大队赤脚医生,我承诺,如果他们因离开计生指导站出了人命,不要你们负责,这总行了吧。孩子已经生出,主人说得斩钉截铁,抓我们的人犹豫着回去复命。
我实在走不动了,那时候县城还没有出租车营运,追兵随时可能会杀回马枪,真是急煞人。县城附近虽有姨娘家可暂住,但那个点已经暴露,我们不敢再去。紧要关头,我二妹急中生智,奔去姨娘家借来一辆人力拖车,她和我老公轮流拉着车,拖起我们娘儿俩,专拣汽车开不进的乡间小道走,星夜奔命回老家。
回到家里,已是下半夜两点钟。
第二天一早,大队支书鲁伯带来六名大汉,不容分说拉走我家所有家具及收录机,然后将主屋封锁起来,把我们全家人赶进旁边一间厨房里住,用柴笆围了个桶大的地方供我们烧饭。
没过几天,大队宣布处罚决定:罚款5400元。称其中5000元是“严打期间”双倍处罚。另外400元,说是因我家已经领过一年独生子女费40元,生二胎罚款十倍。没收我家主屋抵价600元,剩下4800元为欠债待还。那时,孩子他爸当厂医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,我们家是倾家荡了产还背上巨额债务。
经济处罚完了,接着又是行政处分。我老公是“主谋”,大队赤脚医生身份一抹光;我的三妹履职不力犯有“国策罪”,大队妇女主任职务撸掉;我的三妹夫“知情不报”,在乡人武部的工作立马砸锅。连我的老爸(时任乡农机站副站长)也受到了纪律处分。
孩子满周岁时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老公带着我们去本乡砖瓦厂求生存。
全乡通报过的反面典型找事做很难。“夏医生”当铲碳灰工人,已算是发慈悲给了生路。他没有干过重活,每天累得鼻子冒血,但不做不行啊,全家四张嘴等着吃饭,何况还有天文数字般的罚款债务等着要还。厂里给我们住的地方,是粉煤车间隔出的一角,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六年,直到二娃七岁,我们才凑到600元钱把自家老墩子上的主屋赎回,回归相对正常生活。
三妹夫妇丢掉工作也在这里打工。三妹当过小学教师、妇女主任,没吃过苦,在这里干的却是苦不堪言重活。轧砖机把一块块湿泥砖坯吐在机口一张大板子上,再前面是等着运坯砖出去晒的推车,三妹是“搭板工”,负责候在机口把压着许多砖坯的板子及时搭起来放到车上。板子非常重,她需一块接一块不停地搭。有一次不小心迟缓两秒钟,左食指被板子压得鲜血直流连指甲也脱了,疼得她差点晕过去。三妹在砖瓦厂呆了三年多,吃的那苦,我终身感到亏欠她!
读完这段故事,我的心在颤抖。尽管早年对他家遭遇有所耳闻,现在听当事人详尽叙述,我还是感到震撼不已!当年,他们家违计生受严罚全乡无人不晓,欣慰的是孩子死里逃生得以幸存,父母为他取名叫晓存,也许为记住这娃的来历,抑或为记住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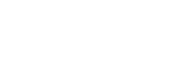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网友评论